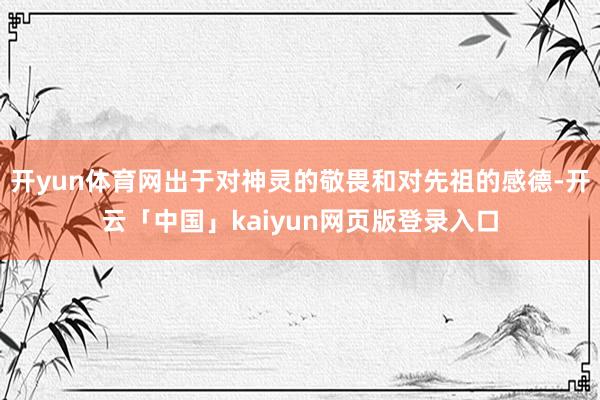|
过年的风趣 □ 丁东 每至春节,总别有一番味谈在心头。——过年,已然成了一种情结、一种隐喻、一种信仰。 过年图个啥?吃喝、玩耍?红包、奖金?约会、团圆?贺年、请安?慰藉、调节?回首、瞻望?……每个东谈主心中各有谜底。其实,在我看来,四千多年来,历经演变,过年的一切,包括备年货、扫房子、贴门神、贴福字、穿新衣、燃炮竹、守岁、祭灶、祭祖、贺年等一个个文化秀丽,一个个过年习俗,皆有它的内在风趣。 为何扫房子?极冷腊月,这天寒地冻的恶劣表象,成了先民性掷中的所有坎,给东谈主以不行先见的厌世胆寒。囿于有限的拒抗严冬和防病治病智商,先民在年关邻近时,效仿皇宫中举行的“大傩”典礼,清扫房子,计帐杂物,掸除灰尘,旨在拒绝疫病冻馁之鬼。此种自带典礼感的作念法,被称为“逐除”。 与“逐除”肖似的是贴门神、贴对联、燃炮竹。据东汉应劭《习惯通义》纪录:旷古时期,在长着一棵大桃树的度朔山上,住着神荼、郁垒两兄弟。每天清早,兄弟俩召百鬼训话,凡是哪个鬼魅晦气了东谈主间,便绑了喂虎。缘于此,东谈主们在桃木板上画上神荼、郁垒的神像,挂于大门掌握,所谓“绘二神贴户掌握”,用以驱鬼避邪。由此,有了“千家万户曈曈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”诗句。及至唐代,因唐高宗珍爱秦琼和尉迟敬德的起因,原先的门神神荼、郁垒被秦琼和尉迟敬德取代。之后,贴门神、贴对联成了过年习俗。 张开剩余70%为何燃炮竹呢?据《荆楚岁时记》载:“正月一日,鸡鸣而起,先于庭前炮竹,以避山臊恶鬼。”由此可见,燃炮竹并非单纯为了文娱,标的亦然驱瘟逐邪。此创意,莫非源自古东谈主点篝火、防野兽的作念法? 大年三十,乃“月穷岁尽之日”。先民为渡过草木不生、食品匮乏的岁末,必须提前储备食品。于是,便有了蒸年糕、蒸馒头、备年货的过年习俗。 年节莅临,出于对神灵的敬畏和对先祖的感德,古东谈主找到了一种既平直又物化的心思抒发样式——祭灶和祭祖。 祭灶,也称“媚灶”,有劝诱灶神的意味。灶神俗称灶王爷、灶公、司命,是玉帝封爵的“九天东厨司命灶王府君”,进展监察东谈主间的泛泛善恶,并在每年腊月二十三(小年)那天上天,向玉帝讲述监察后果。“功多者,三年齿后,天必降之福寿;过多者,三年齿后,天必降之灾殃”。因灶神身份颠倒、神通广大,再加上东谈主们在泛泛生计中未免作念了有违良心的事,牵记灶王爷打小讲述,因而呈上糖果等贡品,敬香祭拜,求灶王爷“上天言功德,下界保吉利”。这一作念法,看似假胆小情,实则出于敬畏。 祭祖是最盛大、最具典礼感的年俗。不但祭品丰盛,况兼流程交集。小辈们在烟草缭绕中,怀着虔敬之心向先祖膜拜磕头,回首祖宗,祈求福佑。祭祖以外,就是给父老贺年,为父老祝福。祭祖和贺年的年俗,很好地解说了“孝”字。之是以这样说,是因为从“孝”的字形看,“孝”由“土”“一撇”和“子”构成,乃“老”“少”和合而成。“土”代表地面,“一撇”代表天降,“子”代表小辈,寓意高下传承,父总是小辈的天。小辈们恰是在祭祖、贺年的精神浸礼中,懂事老到,从而担负起代际接续、娴雅传承的重负。 跟着时期的发展和跳动,东谈主们迟缓脱离驱鬼避邪、看护生命这一浮浅的精神需求。在“万象更新,万象更新”的时期节点、生命驿站,过年早已升华为东谈主们凝听生命回响、细数昨年点滴、祈望来年好意思好的心思请托,其秀丽风趣庞大于履行风趣。 于是,大扫除、贴门神、贴对联、贴福字、燃炮竹、穿新衣等年俗,只是成了东谈主们营造年味、编织想象的有用款式。原来为渡过年荒而储备的年货——年糕、馒头,已背离了吃的初志,仅存“高——年年高”“发——年年发”的寓意;那些世俗草率吃、过年还是吃的吃食,被赋予了讨喜的雅号:“如意”(芽菜)、“元宝”(蛋饺)、“频年有鱼”(鲢鱼)、“凤爪”(鸡爪)、“百财”(白菜)、“聚财”(荠菜)、“团圆”(汤圆)、“金瓜”(南瓜)…… “故地整宿念念沉,霜鬓明朝又一年。”(高适《年夜作》)手脚一种强盛的文化存在,年俗在历史长河中绵延了数千年。现如今,东谈主们总惊叹过年的氛围不浓,以至称“春节”为“春劫”,那是物资富余、精神穷乏的起因。试问,当过年皆成为贫困或鸡肋的时候,那咱们生计的风趣究竟是什么? 有句话说得好,“有钱没钱,回家过年”。因为,即便路线远方、餐风宿露,在家哪怕只是住上彻夜,吃上一餐,这职责极力中的一次抽身、跋涉兴奋中的一次停顿、精神窘迫中的一次安危,何尝不是岁月的静好、东谈主生的愉悦和重启的私密?! 著名作者冯骥才曾说,用生计追求愿望,用愿望点火生计。过年,不单是是浮浅的过节,其本色是精神的、守望的,蕴涵着巨大的亲和力和凝华力。它既是中华英才生命追求的精神解救,更是中原儿女心思开释的贪嘴盛宴。 发布于:江苏省 |